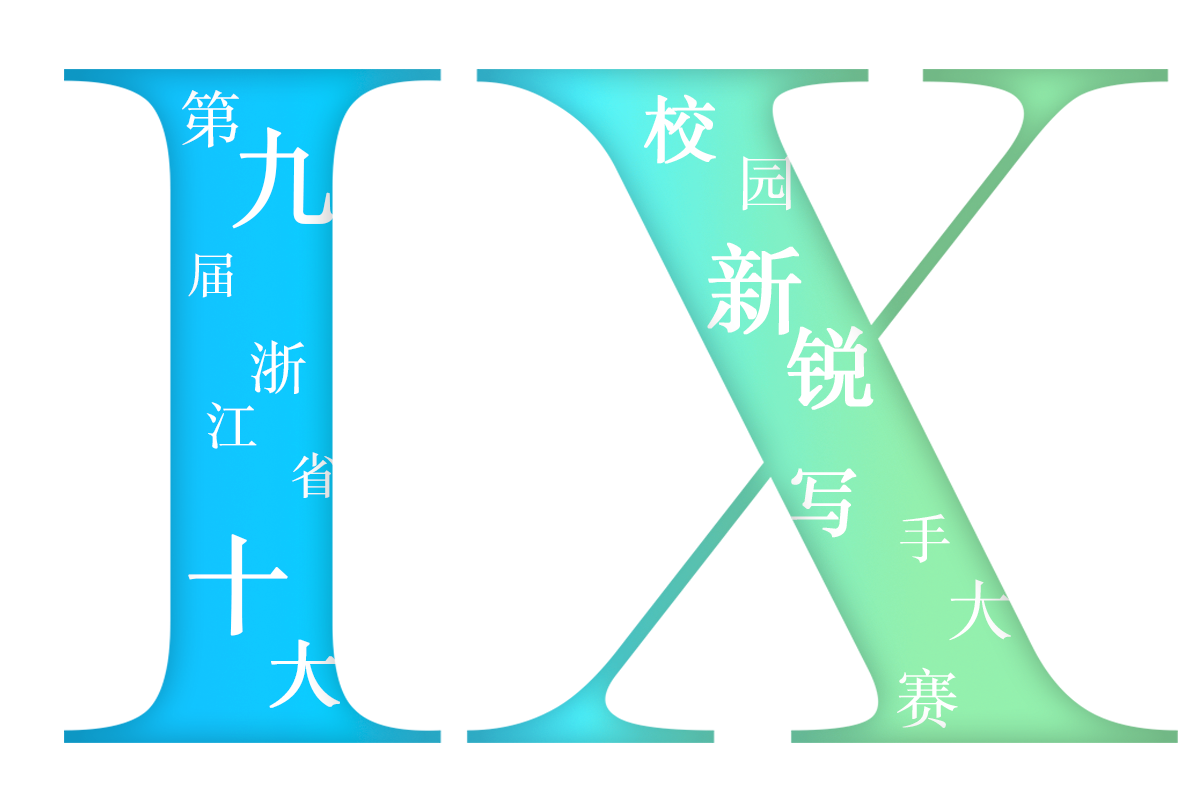索诺拉旋转
无音无字歌 发表于 2024-06-21 22:56:14 阅读次数: 1962不是符号,是岁月。
它们说它们说的话,
我们说的名字
说着时间:它们说着我们,
我们是时间的名字。
“窗外是什么?”我问马尔克斯。
“一颗星、一张纸、一片空白。”(引自波拉尼奥《荒野侦探》的结尾)
我感到喉咙愈发干涩,皮革与黄沙附着在大脑的皱褶中,逐渐渗透了思路与脉搏,“你知道我没有在谈论波拉尼奥。”
“ 那你是什么意思?揣着本《荒野侦探》就过来朝圣的Cultureta。”(注:俚语,类似中文的‘文青’)她猛吸了一口卷烟,左手娴熟地换挡, “而且,别叫我马尔克斯,我们这儿姓这个的忒多了——叫我罗塞塔或者罗莎都行。”
她的声音沙哑而高亢,像一只饥渴的乌鸦。时不时从前座投来的目光,如鸟类尖锐的喙部般毫不留情地戳穿了一切,这份锋利和着西班牙语特有的明烈与迅捷在车内扩张,与此同时沿途的沙漠也变得沉默又凶戾。
我尝试发出罗塞塔名字里的‘r’音,可惜弹舌实在不在我贫瘠的语言系统收录范围之内,只好悻悻闭上了嘴,指了指车窗之外。
那里有一支车队。
罗塞塔挑起了未经修剪过的眉毛,似乎骂了一句我没学过的西语脏话。
“是偷渡者。”她用汉语一字一顿地告诉我,“我们得避开,被牵扯进去准没好事儿。”
我紧张地坐直了身子,把水瓶攥得很紧,“怎么办?”
她看了眼手机上离线保存的地图,朝我晃了晃。
“我发小的长辈在离我们西南3公里的墨西哥沙漠区有一家休息寓所——我想你不会执着于荒野求生的。”
“方便的话我们就去那里住几天吧。”我看了眼东面离我们越来越近的车队,总算松了口气。
罗塞塔不置可否,只是调转车头,踩下油门。
引擎的轰鸣声伴随着远处的几声枪响,透过热浪在沙漠中蔓延,转而又被迅速吞没。
(一)
状况不太好,马尔克斯的车死死陷进沙中,我们只得下车步行。
所幸这里并不是索诺拉沙漠的深处,邻近墨西哥城的地理位置使我们的手机与导航仍有微弱的信号,而寓所业已出现在视野中。
我开始后悔携带这么多书同行,即使有罗塞塔帮忙分担重量,这份知识的负担对于徒步在沙漠的人依旧十分不友好。
“我当初提醒过你的。”她叹了口气,十分老成地拍了拍我的肩。
马尔克斯·罗塞塔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社会科学与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,申请了gap year后就在各地游览,后来因为一些私人原因提前回到了墨西哥。一个月前,我看到她发布在社交网站上替异国游客当向导的帖子,经过私聊初步确认了安全性与真实性后,我们成功定下了这次旅行的计划。
在私聊中,我得知马尔克斯辅修汉语,并且想要把这段时间的向导经历当做素材写进课题作业中,并顺带提升中文水准(即使我们交流更多用的是英语),所以向我收取的费用几近于无。
她在听闻我“因为热衷于波拉尼奥,而想进入索诺拉沙漠看看”后发表了一句短小精悍的评价——Babieco!(蠢货)
青年诗人马德罗加入了一个名为“本能现实主义诗派”的地下群体后,跟随诗人利马与贝拉诺从墨西哥城出发深入索诺拉沙漠,去寻找上世纪先锋派女诗人塞萨雷亚·蒂纳赫罗的踪迹——《荒野侦探》,一本非常规的公路小说。
我当时着实是被迷倒了。一股庞大而杂糅的能量,其间包含着梦想与腥燥、热忱与窘迫,深沉的愤怒与浅薄的花哨共存——来源与“文学”与“青春”(其描绘青春的笔触让我莫名联想到了白先勇的《孽子》),潮湿酸热的气息熏得我头昏脑涨。而索诺拉正是承载这股能量的地方。
不过这都是之前的事儿了。
“这么……朴素的吗?”我瞠目结舌,尽量让自己的措辞听上去委婉些。
罗塞塔捋了捋褐色的短发,“不然呢?这里是沙漠,你指望住的多好?不出意外的话,在我们联系的援助人员到来之前都得凑合住了。”
这是一间旅馆,确切来说,是由集装箱搭建而成的废弃旅馆。门牌是一块铁皮,上面喷洒着略显拘谨别扭的拉丁字母:
“Bienvenidos a Sonoran!”(欢迎来到索诺拉)
我在浑浊的烟雾中呛咳着爬起,眯起眼睛下了床,循着来源走去。
罗塞塔正在做早饭,繁复夸张的耳饰在晨光与烟雾的尽头扑闪,传统灶台周围不断升腾起活泼的雾气。
得益于索诺拉区别于其他沙漠的较为充沛的水源,这间寓所有一个水渠、一个简陋的盥洗室、三个房间、一间集厨房餐厅即客厅于一体的屋子,可以满足基本的日常活动。
“你在做什么?塔可饼吗?”我比划着印象中墨西哥卷饼的形状。
她耸耸肩膀,“当然不是,现在可没那么多材料。况且,你比划的是美国那边的改良版本,真正的塔可不是这样的。”
我想到了西方国家的中餐,也笑着耸了耸肩。
“话说,昨晚睡得怎么样?”
“mas o menos,y tu?”我说。
“马马虎虎。”她说。
“我很喜欢中国文化,”马尔克斯坐在小桌的另一端吃着煮好的玉米,用汉语说道,“因为你们的文化和我们墨西哥的很像——就是——不清楚。”
“不清楚?这听上去像是骂人的话。”我蘸了蘸她带来的辣椒粉,“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。”
“在墨西哥,所有人都会在一起——这是天生的,我们就像taco里面各不相同却又密不可分的馅料,有时甚至只要姓氏相同就可以成为亲人。”
四海之内皆兄弟。
“而在每一个周末,只要你还在墨西哥,无论离家多远、手头事务多繁杂,都得回家吃顿饭。”
我忍不住打断了她,“这难道不是一种束缚吗?我们也有相似的传统,不过我这代人大多选择了挣脱这种太过紧密的关系。”
其实来墨西哥半个月前,我写了一份一万五千字的决裂信——给我的父母。他们收到信时的愤怒与茫然与我写信时的情思相仿,我们那时都自说自话地抒发着自己的殷切,没有给对方留下任何余地。
我为各种强行塞进生活中的家庭饭局所困扰,为亲缘关系带来的牵绊而伤神,于是就写下了这份信,作为迟到了五六年的叛逆期的佐证。
“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,所以我选择了出走。”罗塞塔笑起来,“但后来又回来了——这也没什么,主要就是姨夫做的torta实在太好吃了。”
我感到有些难以理解,或者说还尚未体会。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,某个零碎的、镌刻于心灵深处的片段也会带给我这样的体验,但至少不是现在。
我们在日复一日的交谈中挖掘着彼此的共同点,仿佛把对方认作了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,聊得酣畅淋漓。所以即便因救援优先级比较低,需要再等几天,我们也无所谓。
今晚和罗塞塔一起做了顿饭,墨西哥香料口味真的很重,罗塞塔跟我那个湖南室友或许会有在烹饪上的共同语言。
(二)
“李,你和中国的大诗人同名!”罗塞塔兴致勃勃地给我看她的中文课本。
我尴尬地低下头,对于父母给予的姓名感到了一丝羞耻。
虽然从小到大已经因为自己的姓名遭到了很多特殊待遇,比如“天天被老师同学取诗仙的绰号”、“因为名字给别人的印象太深而永远逃不了选修课”之类的,但猝不及防在异国他乡听到这茬还是有些难以接受。
真是的,明明李和白都是很常见的姓氏和用字啊。
我一边这么想,脸却止不住地发红发烫。
“你怎么脸红了?”她看着我窘迫的姿态忍不住发笑。
我试图辩驳:“难道不该脸红吗?这跟西语国家的人叫‘塞万提斯·萨维德拉’‘加西亚·马尔克斯’是一样的道理啊。”
她瞪大了眼睛,“我就叫罗塞塔·加西亚·马尔克斯啊,中间的名字来自于我的外祖父,这有什么奇怪的吗?我邻居还叫费德里科·洛尔迦呢。”
文化差异带来的冲击使我和她之间还是产生了可悲的厚障壁。
我决定不理她一秒钟。
“其实寻找承认双方的相异性也很重要啊。”我躺在硬板床上感叹道。
“嗯?”她不明所以。
“我感觉我之前总是习惯于从你身上寻求与自己的相同点,仿佛只有这样,才能产生一种‘同谋’式的安全感。”
“确实有点啊。但如果像这样把他者完全置于自己的文化想象之中,他者的特殊性不就被剥夺、同化了吗?这样也就失去了对话的意义了吧。”
“正是因为他者的相异性,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不会是字面意义上的融合,而是变成了‘面对面’,这样一种文化才能对其他文化产生吸引力啊。”我打了个嗝。
“毕竟人与人、文化与文化之间对话的目的不该是灌输、纠正或者吞并,而是真正平等的切磋、产生新的理解、迸发出思维的火花对吗?”
“如琢如磨,如切如磋嘛。”
原来沙漠里是可以看到星星的,我一直以为这里除了荒凉只有荒凉。
今天我们自己打了疫苗,毕竟索诺拉这边好像有一些独特的菌种,厨房里面主人留下的面粉快用光了,我和罗塞塔用前几天残留的面粉做了疙瘩汤。
还有就是,我会摊塔可饼了。
(三)
为了纪念在诺索拉的日子,我们决定合写一首诗——她写一句我写一句。
开头是这样的:
“Mi ciudad fue cortada en dos mitades por el viento abrasador/
El sol canta todo el dolor Tristeza y alegría/
En la línea divisoria/”
她的字出乎意料的轻盈、得体,像是轻轻拂过纸面的羽毛。我用蹩脚的西语和翻译器试图转译这段字句:
“我的城市被焚风割裂成浑然一体的两半/
太阳歌唱分界线上一切不存在的沉痛与欢呼雀跃/”
并继续书写:
“话语在歌声中被当做注脚与粘合剂/
毗邻的一半和遥远的另一半由此起承转合/”
马尔克斯把草稿纸拿走了。过了一会儿又拿着西汉词典跑回来,并义愤填膺地对我说:“我不是这个意思,你的翻译糟糕透了!”
好吧。我用韩非子“郢书燕悦”的故事解释,有时牵强附会、曲解原意同样是一种美丽的错误。
是真的很想吃绿色蔬菜了,玉米和腌制肉吃得我想吐。尽管我曾一度嫌弃过绿色蔬菜和稻米。
救援人员来了,帮助我们把车从沙地里抬起来,并修好了坏掉的部分。
抛开一切文艺青年的浪漫想法,我已经难以忍受在沙漠中原始的生活方式——但这一定是一段好的素材,或许某一天我会在创作中用到。
“上车咯,李。”马尔克斯拉开了车门,对我吹了声口哨。
我们驰骋在来时的沙漠中,我突然开口问到:“塞萨雷亚·蒂纳赫罗在哪里?”
“在你脚下,”她欢快地拍打着方向盘,手腕上的链子飞快颤动着,“你这个令人讨厌的小Cultureta!”
附:那首诗歌
我的城市被焚风割裂成浑然一体的两半,
太阳歌唱分界线上一切不存在的沉痛与雀跃欢呼。
话语在歌声中被当做注脚与粘合剂,
毗邻的一半和遥远的另一半由此起承转合。
相同的,相异的;
整体的,离散的——
全部都加入进去混合搅拌。
夜晚的故事由符号底下的岁月拼凑而成,
读者试图在虚假的话语里寻找答案。
请你包容,
这一半的僵化与独断、
另一半的聒噪与敏感。
在索诺拉沙漠中旋转的我和你——
马尔克斯与李白。
“或许我们当时忘记给这首诗取标题了?”我问。
她回消息一直很快,“管它呢。”
(很可耻地投了这篇,不过de nada,原谅我蹩脚的西班牙语,学的语法已全还给某位廖老师了)

 |

 |

 |
范德清 |
张利利 |
汪元 |

|

|

|